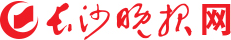老长沙 新味道丨东塘今昔
马笑泉
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,东塘都是长沙的南大门,再往南边走,便算郊区了。1994年,16岁的我第一次独自出门远行,从邵阳来省城读中专。学校在更南边的雨花亭,那时几乎是个城乡接合部。从雨花亭走到砂子塘,也不过十分钟。在我的感觉中,只要到了工人文化宫前,就有了城区的感觉。也就是说,在我的情感记忆中,工人文化宫这一块才算长沙城的南大门。而对于现在出生的长沙人,在他们的认知中,南大门的界限恐怕要再往南推十公里,扎在了原来满目稻禾如今霓虹闪烁的洞井铺。至于雨花亭,那无疑是城区的繁华地带,他们无从想象当年那种略带点荒凉的安静。
当年的东塘早已是长沙的商业中心。这种显赫的地位八十年代就已确立。小时候看全省天气预报,每当报到长沙的时候,东塘百货大楼的英姿就会出现在电视屏幕上。那时我压根想不到,在青春期弥足珍贵的三年中,会离它如此之近。但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,我都没有去那里买过东西。我总认为里面的东西特别高级,特别贵。直到某个星期天的傍晚,我和几个同学去工人文化宫溜冰,在路上碰到一个同学迎面走来。他手里抓着盒牙膏,胳膊甩得特别高。问他从哪里来,他说是去百货大楼买牙膏了,说完还得意地眨眨眼睛,仿佛是在嘲笑我们这几个通常只在学校小卖部买牙膏的土包子。回头盯了他的背影好几秒钟,我终于意识到,我至少也可以去那里买牙膏牙刷的。但那天晚上我并没有顺便去百货大楼逛上一阵,而是泡在工人文化宫的溜冰场。溜冰是男女同学都喜爱的项目,大家都隐约期待有什么故事发生。但故事通常不过是拉拉手而已,还有在女同学尖叫着摔倒时扶上一把。然而光只拉拉手就已无限美好,足以让多年后的我们长久地回味。
我后来在百货大楼不仅买了牙膏牙刷,还买过一副耳机。那时同学中流行“随身听”,巴掌大一个收录机,能别在皮带上。“随身听”多半是去下河街买的,那里有个巨大的批发市场,可以把价格砍得很低。来自下河街“随身听”配上东塘百货大楼的耳机,仿佛传出的音乐声都提高了一个档次。其实百货大楼里更高档的东西俯仰皆是,比如衣服,但那标价是我不敢去细看的。我们买衣服,都是去工人文化宫旁边的服装集贸市场。里面有两层,上百个摊位。五六十元钱能买到一件款式新潮的牛仔服。少男少女们对做工、质料没什么要求,只要款式时髦,就心生欢喜,买回来后,会迫不及待地穿上,在寝室的镜子前自我欣赏一番,然后意气风发地奔赴教室。
1995年,著名的友谊商城进驻东塘,隔着路口立在百货大楼的斜对面。在它面前,百货大楼顿时矮了一截,而且,不那么光芒四射了。但我还是习惯去百货大楼闲逛,对于这个衣着更加光鲜的外来户带有暗暗的抵制。如今友谊商城早已是东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,而百货大楼在气象万千的商潮中也屹立到了今天。长沙市机电厂的退休职工张老在这一带住了五十年,经历了用布票油票肉票煤票豆腐票抢购商品的艰难,也享受到在家里用手机下单然后附近商场超市立刻送货上门的轻爽。他感慨改革开放后,市场经济法则逐步建立,生产、流动多元化了,人们生活才感到便利。而东塘,是长沙最早体现市场经济活跃气象的区域之一,并且一直保持着活力和繁荣。我完全同意张老的看法。就在我中专毕业那年,一座我从未见过的立交桥飞架东塘南北。那时私家车并不多见,但这座通过融资建设的桥,将几年后普遍涌现的路口拥挤问题化解于精确的预判中。
东塘确实有种主动谋划、先人一步的特质。在建立了稳固繁荣的商圈后,又敏锐意识到社区是城市建设的下一个重点,为此任贤使能,不拘一格。像牛角塘社区的王宏霞,一个侗家女子,连事业编制也没有,因工作出色,被任命为社区一把手。她借鉴侗家鼓楼议事传统,创建了塘里塘外议事机制,实现了干部和居民共治。整个社区像侗寨那样清爽,树木成荫,两个小广场受到居民自发维护,木制的凉亭和长廊透着朴素明净的风味。五个民情哨点,值班的都是退休的大爷大妈,不领一分钱补贴却精神抖擞。他们看王宏霞的目光就像看自家的女儿,还会当着客人的面打趣自家书记。想起童年时居委会主任的威风八面,我不禁暗自感慨。领导干部非父母官,也不是什么仆人,最好把自己当成群众的儿女,这样既平等,又贴心,再难的事大家都愿意帮衬,自然能办得熨帖。
采访结束后,区委宣传部的小朱请我在百货大楼后面的背街吃了碗麻辣鸡爪。这号称是雨花区最佳鸡爪,火候确实一流,皮肉既松脱,又有嚼劲。我说,城市需要有机更新。一座城市既要有繁华有序的商场和大道,也要有这样干净又充满日常烟火气的小街小店,让我们随时能歇下来,尝点小吃,聊聊人生。小朱笑着说,还要有那种服装市场。我连连点头。那个服装集贸市场还在。新一代的少男少女像我们当初那样在里面游逛。青春如带露的花苞初绽,而新的时代给了他们更多的选择和体验。想到这些,我既高兴,又有些微微的惆怅。再畅意的故地重游,均难免随之而生的惆怅,这也是一种美好、深切的感情。
>>我要举报